余华向莫言投稿,他将新写的散文《山谷微风》发给莫言,问能不能在公众号发。莫言一开始以为他发错了,后来才意识到,自己的公众号已经有很大影响力了,不禁有些得意,这位“相爱相杀”半辈子的损友,终于也向他的流量低头了。
去年4月,这篇散文在“莫言”账号发布,莫言配了按语,又借用网友调侃他们的两只小狗头像,安在聊天记录里。“莫言和余华的微信头像”迅速冲上微博热搜第一。
莫言已成网络顶流,他的两个公众号办得风生水起。其中,与北京舒同文化艺术研究会会长王振共同运营的“两块砖墨讯”,记录了他们的书法创作,如今也是莫言新作发布最及时的平台。精选自公众号中的诗词、文章和书法,结集成新书《放宽心 吃茶去》,今年8月正式出版。
这本从书名到内容都透露着满满松弛感的新书,记录了莫言这几年的旅行、日常与所思所想。近日,《中国新闻周刊》与莫言聊了聊他最新的写作,也聊了网瘾、松弛感。

莫言。图/视觉中国
“不是号召大家躺平,是号召大家调整心态”
《中国新闻周刊》:这本新书《放宽心 吃茶去》,从书名看就有满满的松弛感。现在年轻人都非常追求和赞赏松弛感,你觉得自己身上有松弛感吗?
莫言:那当然有。我现在已经是70岁的老人了,不可能再像年轻人那样绷得那么紧。但是我也不想彻底躺平,什么都不干了,我还想写东西,还是有对艺术创作的强烈冲动。
之所以用这个书名,是因为既然大家都感觉到很累、很紧张,那不妨放松一下。这并不是号召大家躺平,什么都不干了。有的年轻人会说,我们没有条件躺平,我们还没挣到今天的面包钱,怎么放下?我的意思是说,对已经发生的不可改变的事物,就不要过分纠结了。让它翻过去,我们休整一下,喝喝茶,想别的办法。不是号召大家躺平,是号召大家调整心态,继续战斗,继续工作。
《中国新闻周刊》:很多年轻人感到现在生活中有很多不确定性,不知如何面对,你有什么建议吗?
莫言:没有建议,你要面对现实,因为这不是哪一个人造成的,也没有一个人能够发现一种新的办法,来解决和避免现在社会的很多难题。所以,你只能承认现实,想办法继续往前走。
总而言之,我们既然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,就要承受和面对这个时代带来的一切。我们千方百计想改变自己的命运,但也未必想改变就能改变得了,改变不了怎么办?还是要活下去,要调整心态,改变路径,天无绝人之路,明天太阳还会出来。
我们这本书,就是希望让大家读了以后,能够暂时缓解一下紧张的心情,轻松一下,也许办法就出来了。一个人在焦虑、紧张、痛苦的时候,智商是会降低的,只有平静下来,冷静下来,放宽心以后,你的智商才会恢复到原有的水平,甚至超水平发挥。
《中国新闻周刊》:你还是挺自谦的,没有说通过这本书要教大家什么。
莫言:我从来不以教师爷的态度来对待读者,而且我也烦这样的一种态度。假如一本书摆出一副教师爷的姿态来,那我根本不会看的。如果我的书里有这样一种态度,我想读者也不会买账。
一个人把自己设想得高高在上,想到我是什么功成名就的大作家、大知识分子,就自然很难平等地跟老百姓一样思考问题。几十年前我说过,我是作为老百姓来写作,不是为老百姓来写作。当然有人要为老百姓写作,没有任何问题,我举双手赞成。但我自己觉得,我就是作为一个老百姓来写作,我时刻提醒自己。
进一步从创作的观点来讲,对待书中的虚构人物也要持一颗平常心。人物一旦确立,就有自己的性格,有自己的发展方向,有自己的命运,不一定是作者可以去扭转的。一部长篇小说写到三分之二,就不是由作家来支配人物命运了,而是人物按照自己的命运往前走,甚至会跟原先的设想大相径庭。
《中国新闻周刊》:《不被大风吹倒》和《放宽心 吃茶去》虽然看起来好像是在写自己的旅行经历、人生感悟,但其实对当下的社会情绪也有明显的呼应。这是你自己有意的想法吗?
莫言:这是我的观察,也是我的感受。你说什么时候是最好的时代?往往都是过了多少年以后,才怀念某一个时代。搞文学的都在怀念20世纪80年代,我回忆了一下,其实我们当时也有很多不满意、不如意。大家对当下可能有这样那样的不满,但如果再过去一些年,对今天这个时代没准也有很多的怀念和回想。
任何事物都没有十全十美。尽管很多人有诸多不满意,但时代和社会总是在进步,不是像火箭那样“轰”的一声就上去了,而是螺旋式的。河流有时候往西拐了个弯,但最终还是千回百折,向东流到大海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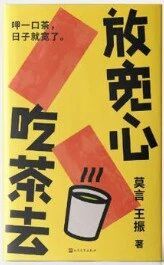
“网瘾老人”的反思
《中国新闻周刊》:你之前有一个短视频很火,说自己一边刷短视频,一边懊悔,后悔时间又浪费了。你现在会对网瘾感到焦虑吗?
莫言:经常自责。我看短视频,一看半个小时过去了,必须立刻停止。还是有自觉性的,要不就完全成瘾了,无法控制自己。我看过一个视频,一个三四岁的小孩,当妈妈把手机从他手里拿走的时候,那种疯狂的发泄、哭嚎,让我很震惊。
这个玩意儿对人的影响太大了,一条一条往下翻,时间就这么过去了。它带来很多新的信息,但一不小心也会因为人的本能而被它带着走。最大的问题是,如果你老是刷一类东西,平台就不断给你推同样的东西,结果让人变得偏执。你获得的只是你想看的东西,别的你都不知道了,看起来好像掌握了很多信息,其实也许不如以前对社会认识得全面。
《中国新闻周刊》:面对这种技术“巨兽”,个人能做什么?
莫言:个人没法反抗,像我们这些成年人,还是有点自制能力的。就不断提醒自己,该干别的事儿了,该看书了,该写作了,不要沉溺得不能自拔。90%的人都能头头是道讲出短视频对人的危害,对创造性劳动造成的伤害,对精神生活造成的伤害,但好像没有一个人能够完全戒除网络,将来可能会慢慢发展成一种新型的精神疾病。
《中国新闻周刊》:现在大家的阅读也越来越碎片化。这几年你写了不少散文和诗词,你的写作有一种篇幅缩短的趋势。你怎么看待写作的长短和表达的关系?
莫言:小说该长就长,该短就短。我写过五六十万字的长篇小说,也写过很多几百个字甚至几十个字的小小说。这两年,我还集中精力写了一些超短的小说,叫《一斗阁笔记》。短的小说思想含量、艺术含量未必少,几十个字可以让人回味无穷,而有的长篇小说几十万字读完,可能还不如《聊斋志异》的一个小故事给人的启发更深刻。
但是长篇小说自然有它不可代替的伟大之处,很多中国作家都认为,一辈子总要有几部自己比较满意的长篇摆在那儿,而且在经典作品当中,长篇小说占的比重最大。我写过长篇、中篇、短篇、超短篇,也写过诗词、戏剧,如果让我这一辈子什么都不许写,只能写一种文体,可能还是长篇小说。
记者:倪伟
编辑:杨时旸